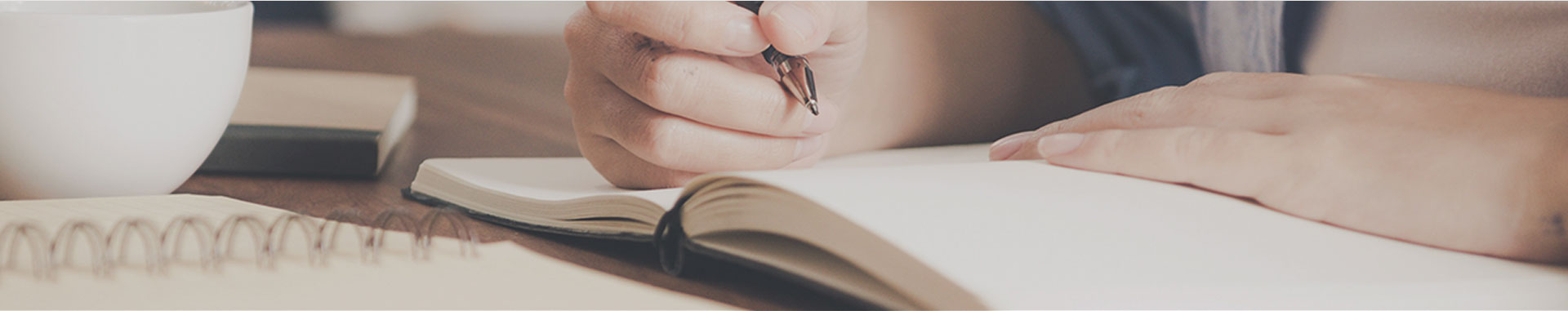
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土豆是极其普通的一种蔬菜,但是我却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得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新年的余温尚未散尽,走亲访友的喜悦还挂在眉梢,农人们便开始了劳作。等到遇上晴好天气时,父亲便走向屋檐下,去拿悬挂在那里的去年留存的土豆种。它们在竹筐里静静蛰伏,历经寒冬,却怀揣着春日新生的梦想,长出了嫩黄的小芽。
父亲取下竹筐,动作轻柔地将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土豆种捧在手中,细细端详,眼神里满是期许。若是个头较大的土豆种子,父亲便用菜刀细心地将其切成小块,每块都保留一个芽眼,切面处粘上草木灰以防病菌感染。
母亲也没有闲着,她脱下棉鞋,换上褪色的解放鞋,随后找来畚箕,从猪圈里挑起满满一担猪粪。猪粪是父母将稻草垫于猪圈里沤造、积攒多时的肥料,黑黝黝、沉甸甸,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母亲迈着稳健的步伐跟在父亲身后,向着村东头那片向阳坡地走去。
来到自留地里,父亲先用锄头翻整土地,将土疙瘩轻轻敲碎,把杂草连根拔除,然后开始挖坑。父亲手中的锄头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每一下都精准有力,不一会儿,一排排整齐的土坑便出现在眼前,宛如等待检阅的士兵方阵。母亲则将猪粪均匀地撒在地坑里,为即将播种的土豆种铺就一层有营养的“温床”。随后,父亲将土豆种轻轻放入坑中,再细心地盖上泥土,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饱含着温柔与慈爱,就像在呵护自己的孩子。
土豆种下去之后,每天早上起床后父亲都要去地里转悠,当看到破土而出的嫩绿小芽时,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时间一点点地溜走,土豆苗也一天天长高、长壮。待到四五月间,土豆花便绽放了,小小的花朵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娇俏,微风拂过,轻轻摇曳,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芒种过后,土豆便迎来了收获的季节。父母带着我和弟弟早早来到地里,父亲挥动锄头,小心翼翼地挖开泥土,一颗颗圆滚滚、胖乎乎的土豆便呈现在眼前。它们或大或小,或白或黄,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母亲和我们跟在后面,将挖出的土豆一个个捡起放进筐子里。每捡起一颗土豆,就像是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幸福。
将土豆拉回家后,母亲会把它们分好类。破皮或者个头特别小的土豆用来喂鸡和猪,品相完好、饱满圆润的就小心翼翼地存放好,留作一家人日常食用。
有时候,母亲会给我们做土豆炖排骨。她先将排骨焯水,捞出后控干水分。接着往锅中倒油,下入冰糖炒至枣红色(冒小泡),然后立即倒入排骨快速翻炒上色,再下入姜、蒜、八角、花椒、香叶、干辣椒等炒出香味,之后加开水没过排骨,调入老抽、生抽,用大火炖30分钟。时间一到,母亲便倒入土豆块,加盐后继续炖15—20分钟,直至土豆和排骨都变得软烂即可。刚出锅的土豆炖排骨香喷喷的,引得我们垂涎欲滴,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得津津有味。
有时候,母亲还会给我们做美味的油煎土豆。她先将个头较小的土豆去皮,放入锅中煮熟,随后捞出沥干水分,置于盆中备用。接着,母亲在烧热的菜锅中放入半勺猪油,将煮熟的小土豆倒入锅中,撒上少许食盐。待小土豆煎至四面金黄时,再撒上些许辣椒粉和葱花等佐料,轻轻搅拌几下即可出锅。煎好的土豆香气扑鼻,吃一个满口生香,令人回味无穷。
母亲最常做的还是炒土豆丝,不仅简单易做还好吃。每次炒土豆丝之前,母亲总会将切好的土豆丝盛装在网筛里,放入清水中浸泡几分钟,这样能洗掉土豆中的淀粉,使炒出来的土豆丝更脆。
那些沉淀的淀粉也有大用处,母亲会先将水倒掉,用锅铲铲出淀粉,然后放在太阳下晾晒。当淀粉积攒到小半布袋时,母亲就会拿来做土豆粉。她先往土豆淀粉中加入适量的水,然后轻轻按压、揉搓、折叠,原本松散的土豆淀粉逐渐融合,变成了光滑而有弹性的面团。接着,母亲将面团放入木质漏瓢里轻轻拍打,只见一根根细小如丝的土豆粉条,如同灵动的小精灵从漏瓢底部欢快地钻出,争先恐后地掉进滚烫的开水锅中,在那里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当土豆粉煮熟后,母亲将其盛在碗里,浇上一勺自家熬制的浓汤,再洒上少许辣椒油、葱花、油炸花生米,一碗美味的土豆粉便制作好了。吃土豆粉时,最好配上母亲腌制的咸菜,那简直是人间至味。夹起一筷土豆粉送入口中,爽滑、劲道,那独特的滋味从舌尖一直暖到心底。
土豆没有华丽的“外表”和高贵的“出身”,宛如一位默默守护的乡村老者,用它的平凡与伟大,诠释着生活的真谛——无论风雨如何侵袭,只要有土地在、有双手在、有希望在,就能在岁月的土壤里种出幸福的果实,让爱与温暖在时光中绵延不绝。
 电话: 010-87293157
电话: 010-87293157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洋桥70号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洋桥70号
版权所有 @ 2023 中国食品杂志社 京公网安备11010602060050号 京ICP备14033398号-2

 1612
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