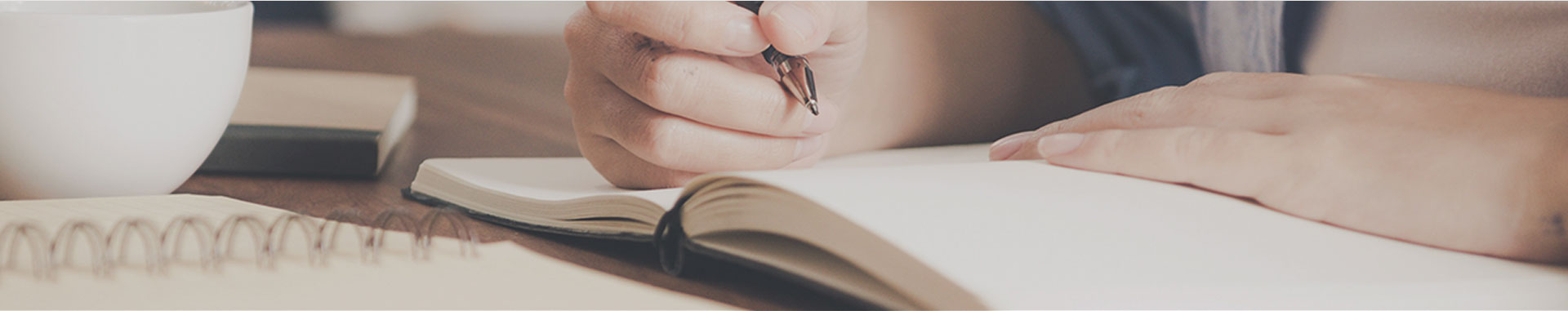
位于南疆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风沙掠过龟裂的土地。一支驼队正缓缓西行,此起彼伏的驼铃声打破了寂静。旅人们的褡裢里装着的不是金银,而是几枚坚硬如戈壁石的圆饼——馕,每当指尖拂过粗粝、焦黄的表面,一种奇异的安稳便从掌心弥漫开来。他们掰开馕饼,那“咔”的一声脆响,竟似劈开了荒漠的孤寂,麦粒深藏的暖意与地火的魂魄,瞬间在舌尖绽放。
馕的诞生
关于馕的初生,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烈日熔金的某日,牧羊人吐尔洪被骄阳灼得头昏眼花,情急中将妻子放在盆中的湿凉面团扣在头顶,飞奔向羊群。途中,吐尔洪不慎被红柳根绊倒,面团摔碎于滚烫的沙地,奇香骤起,弥漫四野。他拾起一片入口,焦壳爽脆、内里松软,难以言喻的麦香安抚了所有燥热。他包起碎饼奔回村落,见人便分享一片,收获无数“好吃”的惊叹。当众人欲为这神奇食物命名时,吐尔洪脱口而出:“就叫它‘馕’吧!”从此以后,这朴素的名字便在大漠与绿洲间扎下了根。

偶然间发明了馕的吐尔洪并未止步于此,在阴霾或寒冬无法获得阳光的恩赐时,他便在自家院中掘地为炉,四壁抹上黄泥,投入红柳根燃起熊熊烈火。待炭火炽红,他将揉好的面团迅疾贴向滚烫的坑壁。须臾间,奇异的焦香升腾,远超日晒之味,一种更浓烈、更恒久的生命滋味,在泥土与火焰的交融中诞生了。这深藏于大地的火炉,宛如一个炽热的子宫,默默孕育着金黄、焦香的奇迹。
其实,这深埋黄土的馕坑,其历史也很悠远、厚重。从截至目前所获考古资料来看,真正意义上的馕坑最晚应出现于汉晋时期,到隋唐以后,随着馕的形制等发生巨大变化,馕坑基本趋于完善,并一直沿用至今。
千余年光阴流转,从最初掘地为坑的粗朴,到以生硝提升火候与保温的智慧,再到如今陶瓷内胆、铁壁新能源的精准调控,馕坑的演变史,正是一部微缩的新疆先民与严酷自然相搏、相融的生存史诗。
馕的制作
走进任何一户维吾尔人家的庭院,空气里必氤氲着面酵的微酸与期待。发面,是与时光的第一次郑重“对话”。冬季寒冷、漫长,需要五六个小时的守候,室内炉火轻燃,维持着20℃的暖意;夏季阳光炽热,则只需两小时光景。主妇深谙发酵之妙,面若醒发过久,酸味刺鼻;时辰不足,则僵硬难食,酵头的多寡全在指尖与鼻息的微妙感知里。
面发好后,揉捻的功夫更见真章,面团在粗粝、宽厚的手掌下被反复推压、折叠、摔打。揉,必须要匀透,只为“唤醒”麦筋的韧性。揉的次数愈多,馕的“筋骨”愈是强健,香气愈能穿越漫长时光而不散。
揉好的面团被分成大小不一的剂子,巧手翻飞间,面剂在案板上被塑造成形。有的如圆凳面般宽薄,直径可达半米,边缘敦厚如壁垒,中心薄脆且饰花纹,此乃“馕中之王”,用于待客的“艾曼克”;有的小巧如杯口,厚约一厘米,做工极尽精微,此乃“托喀西”;有的中间留孔、形制朴拙,这是“格吉德”……
面坯初定,指尖蘸取清油或蛋液,再轻灵地点缀芝麻、斯亚旦(黑草籽),或嵌以葡萄干、碎核桃。这不仅是味觉的叠加,更是视觉的诗篇——食物之美,原可如此丰饶。

与此同时,院角的馕坑正经历火的洗礼。打馕的师傅眼神专注如鹰,他深知火候是馕之魂魄,待坑壁烧成灰白,炭火炽红,便到了最需拿捏的关头——撒盐。细白的盐粒扬入火坑,“嗞啦”声起,青烟倏忽腾升。这一撒,是调节坑温的古老密钥,是防止面饼滑落的天然粘剂,更是唤醒谷物深层甘甜的秘咒。风门开合间,热流被“驯服”,均匀地包裹坑壁,静待面坯的降临。
贴馕的刹那,是力与美的绝唱。打馕的师傅探身向那灼热的深渊,手臂稳如磐石。蘸过盐水的馕在他掌中翻飞,湿面坯“啪”一声脆响,服帖地“吻”上滚烫的坑壁。此套动作行云流水,仿佛不是劳作,而是与火共舞的仪式。
坑盖落下,将烈焰与麦香一同封存。打馕的师傅凭经验掌控时间,偶尔掀盖观察,金黄的色泽在热气中悄然蔓延。等到火候到了,师傅拿起如套马杆的铁钩,轻巧地勾起那枚枚金黄的“月亮”——边缘如少女裙裾般蓬松,中心像铜锣般脆亮。刚出炉的馕,需再刷一层晶亮的熟油,那光芒,仿佛熔化的阳光被锁在了麦香里。

刚出坑的馕,是感官的盛宴。指尖触到微烫的焦壳,一声脆响应手而开,热气裹挟着纯粹的麦香喷涌而出,瞬间侵占鼻腔。咬下一口,外壳在齿间碎裂如秋叶,内里却柔韧如春绸。若遇油馕,羊油的丰腴悄然融入;肉馕则是孜然与羊肉在口腔点燃的狂欢;千层馕(卡特力玛)薄如蝉翼,层次间藏着酥油与时光交融的密码;抹了冰糖水的“酉克曼馕”,亮晶晶如裹了琥珀,甜意清浅、悠长……
馕的意义
在新疆,馕早已超越果腹之物,沉入维吾尔人精神的河床。它见证了人生的很多重要时刻,如在婚礼上,新人同食醮过盐水的馕,宣告着共担风雨、白首不渝的盟誓。它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与共生,馕渣绝不践踏,必郑重拾起置于高处,“让鸟儿也分享大地的恩慈”。一句古老箴言道尽馕在族群心中的分量:“馕是信仰,无馕遭殃。”库尔班大叔欲骑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的传奇里,行囊中那一大袋耐储的馕,是老人朴素、深情的物质保障,更是穿越戈壁的信念象征。

如今,无论是喧嚣巴扎还是宁静村落,馕坑的烟火气从未断绝。打馕的师傅们盘坐坑边,身影在热浪中微微摇曳,铁钩起落间,金黄的馕饼如旭日般被一枚枚钓出火海。作坊里,年轻学徒的目光紧随着师傅的每一个动作,揉捏、贴壁、观火、起馕……这门古老手艺,在炭火噼啪与面团拍打的节奏里,正被无声地传递。纵有现代化电馕坑带来便捷,那由黄泥、红柳与千年经验构筑的传统馕坑,依然倔强地吞吐着烈焰。它烤出的馕,有着一种无法复制的、带着泥土与烟火烙印的魂魄之香。
晨曦微露,第一缕阳光刺破戈壁的沉寂,新的面酵已在盆中悄然萌动,新的炭火即将在馕坑里点燃。这源自波斯、扎根天山南北的古老面食,早已将它的根须,深深扎进这片土地的肌理与血脉。它朴拙如大地,炽热如火焰,坚韧如胡杨。一枚馕,就是一团凝固的日光,一捧大地的馈赠,一首用麦粒与炭火写就的、流淌在丝绸之路上的生命长诗。掰开它,便掰开了千余年风沙也未能掩埋的、属于绿洲的温热心跳——那是炉火不熄的承诺,是穿越时间荒漠的、永恒的馕之情。
 电话: 010-87293157
电话: 010-87293157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洋桥70号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洋桥70号
版权所有 @ 2023 中国食品杂志社 京公网安备11010602060050号 京ICP备14033398号-2

 3548
3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