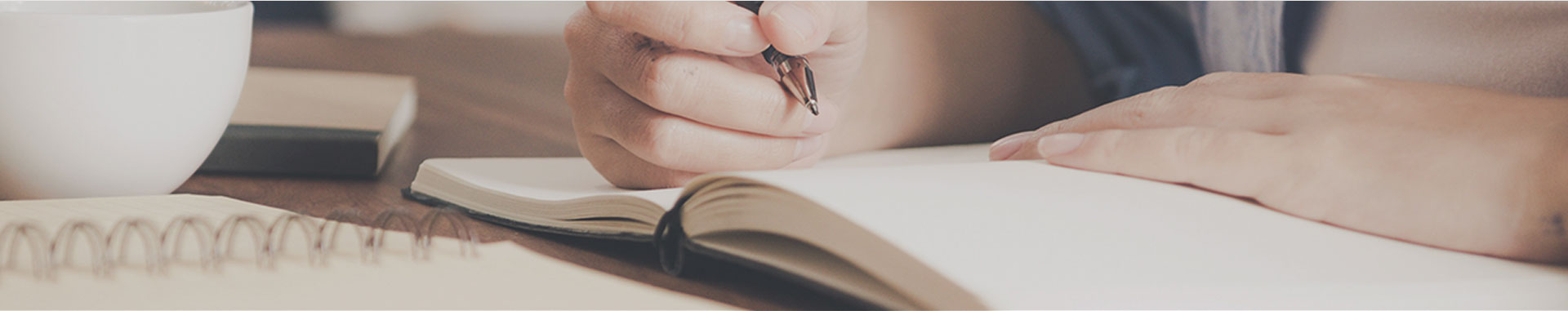

在中国的烹饪史册中,刀工占据了光辉的一页,自古以来就受到事厨者的重视。其实,烹饪刀工技艺自石器时代便已存在,原始人类打制的刮削器、切割器等,就是最原始的刀工工具。后来,历经时代的更迭,事厨者代代口耳相传、师徒传承,并不断守正创新,逐渐形成了更合理、更科学的体系性刀工技艺。可以说,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食物形态,全是历史积淀的结果。
刀工自古就受重视
在烹饪中合理运用各种刀工方法,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食材快速成熟。可以说,用最佳的食材形态来适应相应的传热介质,是烹饪刀工追求的本质。
中国烹饪从古至今都在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最优的食物形态,以适应不同的烹调技法,再通过火力大小和烹饪时间长短,使菜肴的“质感”(俗称“口感”)达到适口的界限或范围,即“阈限值”。比如外表光鲜、色泽亮丽的肴馔,却因食材大小、厚薄不匀导致生熟不匀,使人咬之不断、嚼之不碎,必然难以下咽。所以,“刀口到家”对菜肴质感的影响是显著的,只有将食材切成符合并适应烹调要求的形状,才能使各类菜肴达到最佳的质感。
我们在烹饪古籍中常能见到“断割”“割烹”“割灸”这样的词语。《周礼·天官》中记“内饔”的职责时,称其负责“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代表刀工的“割”,排在了代表加热的“烹、煎”和代表调味的“和”之前,说明了刀工的重要性。
《孟子·万章下篇》中亦有“伊尹以割烹要汤”。其中,“割烹”指切割、烹调等厨艺,“要(yāo)”意为求取或谋求,“汤”即商朝开国之君商汤。这句话的字面含义为,伊尹通过高超的烹饪技巧接近商汤,以此获得重用,这便是“至味说汤”的故事。这里仅用“割烹”二字表达了治食的精要所在,一个字表示刀工,一个字表示熟制,既反映了古人的惜字现实,又进一步表明了古人早已对烹饪中切割的重要性有所重视。
《礼记·内则》中介绍古代“八珍”之一“渍”的制作方法时提到:“取牛肉必新杀者,薄切之,必绝其理。”这里的“理”指的就是牛肌肉纹路,“薄切之”则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切割要求。《礼记训纂》载陈大言:“绝其理,横断其文(纹)理也。”这里清楚地解释了《礼记·内则》中“绝其理”的意思,也就是刀法中的横纹切,业内行话叫“顶刀切”。这证明了先秦时代在进行肉类食物的切割处理时就存在经向与纬向的区别,侧面说明了刀工的本质意义和重要性。
孔子在《论语·乡党》中也记有饮食训条,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割不正不食”等,这些都是讲究成菜刀工要求的体现。
“食不厌精”的要求,反映出孔子所倡导的精品意识,可以看作是对食材加工求精求细的具体化。时至今日,餐饮从业者应以“精”为目标,从食材选择到切配加工成成品,再到用餐场地与环境氛围的营造,都将“精”字贯穿其中。
“脍不厌细”的要求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这里的“脍”,是指细切的肉或切肉的过程。我们知道,“厌”的其中一个释义是满足,如今人们多用这个意思解释此处的“厌”。这四个字的总体意思是,切肉时不要嫌麻烦,一定要追求精细。
肉之所以要细切,除了有审美和进食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是传热介质的需要。肉在受热时,其表层的温度场与内层的温度场有所不同,表层温度高,其内层温度要低。那么,如何让内层和外层的温度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一致,使烹制的生肉尽可能在同一时间成熟呢?最优措施就是将食材分解成小的形体,形体越小,食材内层和外层温度场的差异就越小,才能更好地保证肉的内外在同一时间成熟,从而让入口触觉、味觉感受,甚至于在汲取营养量等方面得到最大优化。
“割不正不食”的要求,也包含了深刻的烹饪哲理。其中的“不正”一词,是指丧失了菜肴外在的美观,即食材没有做到大小一致、厚薄均匀,切割没有达到“正”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将烹饪由生理上的满足上升到心理上的享受,把烹饪的外在美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烹饪刀工总要求的先贤。
庄子在《养生主》里讲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对先秦时期的切割之术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庖丁”也成了技艺超凡事厨者的代称。其实,这种切割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分档取料”技艺,是世代传下来的手艺。
古籍中的高超刀工技艺
那么,古代事厨者的刀工技法到底有多高呢?其实,诸多古籍中就有相关描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三国时,曹植在《七启》中描述了宴席上的精妙刀工:“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如叠縠,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意思是,切割后的物品(如鱼脍、丝帛)薄如蝉翼,近乎透明,能将纤维分解至最细微的程度;切割后的物品层层堆叠,如同折叠的縠纱,既轻薄又富有层次感;切割后的碎片如雪花般松散飘落,形容其轻盈飘逸之态;切割后的薄片轻得能随风飞舞,而刀刃却无需反复转动或用力,凸显刀法的流畅与高效。
东汉傅毅在《七激》中描写了惊世骇俗的刀工技艺:“涔养之鱼,脍其鲤鲂。分毫之割,纤如发芒。散如叠縠,积如委红。殊芳异味,厥和不同。”意思是,池塘中精心养殖的鱼非常鲜嫩,事厨者将鱼肉切得极薄,细如发丝尖端,轻薄如纱,搭配不同调料会形成独特的风味。
晋代张协的《七命》中也有描绘刀工技艺之精妙与食材之鲜美的句子:“尔乃命支离,飞霜锷。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娄子之豪不能厕其细,秋蝉之翼不足拟其薄。”意思是事厨者的刀刃如霜雪般寒光凛冽、锋利迅捷,肉类被切割后,其肌理细腻如散落的锦缎,白色肉片比蝉翼还要薄,如雪花飘落。
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出自晋代潘岳《西征赋》中的名句:“饔人缕切,鸾刀若飞;应刃落俎,霍霍霏霏。”这里描绘了事厨者操刀切脍的过程,带铃的刀发出有节奏的悦耳之声,刀落脍飞,彰显了刀功、技能之娴熟。事厨者操刀姿态及动作之优美、功夫之高强、专注之敬业,皆令后人赞叹不已。
唐代诗人杜甫在《观打鱼歌》中也曾描写过川人厨者的刀工技艺:“饔子左右挥霜刀,鲙飞金盘白雪高。”意思是说,事厨者挥动着利刀,切得极薄的鲙一片片飞舞落俎,盛在华丽的盘中,像堆着的雪一样洁白。
唐代时还出现过一本谈论烹饪技艺中刀工的专著,名叫《砍(斫)脍书》,可惜是个手抄本,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虽然原著已失传,但是在明代博物家李日华写的《紫桃轩杂缀》一书中,可见其部分风貌:“祝翁……家传有唐人《砍(斫)脍书》一编,文极奇古。首篇制刀砧(打制厨刀和选择砧板或木墩的要求,笔者注),次别鲜品(择选鲜活的食材要求,笔者注),次列刀法(依食材性质施用刀法,笔者注)。有小晃白、大晃白、舞梨花、柳叶缕、对翻蛱蝶、千丈线等名,大都称其运刀之势与所砍细薄之妙也。”从这段话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唐代事厨者的刀工技艺已十分娴熟,可以灵活施用各种刀法,并据此取了多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
明朝书画家董其昌曾作打油诗,把前人描述过的刀技写得既通俗又夸张:“主人之刀利且锋,主母之手轻且松。一片切来如纸同,轻轻装来无二重。忽然窗下起微风,飘飘吹入九霄中。急忙使人追其踪,已过巫山十二峰。”意思是主人所用的刀具极其锋利,切割后的食材薄如纸张,突然而来的一阵微风竟然将食材吹到了九霄云外。
清代时,我国烹饪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袁枚写了一本简约、精炼的美食杂记——《随园食单》,系统记录了中国14—18世纪的烹饪技艺、饮食理论及南北菜肴,被国际食学界誉为“中国古代烹饪宝典”。然而,这本书里却鲜有关于刀工技术方面的论述,唯一提到的一次是在《洁净须知》章节里:“良厨先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但是,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刀具的洁净,而不是刀工刀法。至于袁枚为何没有提到刀工技法,我们不得而知,作为一种悬念,让它且保留一份玄学上的神秘吧。
之所以选录这些古籍,是为了证明“烹饪自古重刀工”的结论。古代的文人把我国烹饪刀工技艺渲染得如此淋漓尽致,并运用了大加赞誉和夸张的艺术修辞手法,这些虽不可全信,但也一定是有历史事实依据的。
中国的烹饪刀工技术经过历代司厨人员的承袭和创新,发展至今已构成了系列化、系统化和完整化的施刀操作体系,形成了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践应用为核心的烹饪学分支学科。希望当代的从厨者能够把发扬古代匠心精神、传承非遗文化视为己任,推动中国烹饪刀工技艺再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简介
李刚,北京市第一零三中学(职业高中)原校长、北京酒店管理职业学校原书记兼校长、职业教育特级教师、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育专家。从事职业教育工作45年,撰写出版专著和主编国家规划教材10余部,主持国家/省部级教育教学科研项目5项,以优秀等级结题。曾获“北京市十大杰出人民教师”、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北京市教育系统“教育之星”等称号,还在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评选中荣获一等奖3次。
 电话: 010-87293157
电话: 010-87293157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洋桥70号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洋桥70号
版权所有 @ 2023 中国食品杂志社 京公网安备11010602060050号 京ICP备14033398号-2

 656
656